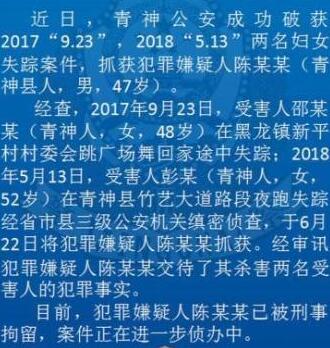女子40岁裸辞在家当全职女儿 原因竟是这样太无奈了
导读:但“全职儿女”所带来的压力是她没有想到的,从开始需要缴纳社保,母亲的抱怨就与日俱增,开始变得挑剔和苛刻,“她经常说想去旅游但不能去都是因为我,如果我说我可以自己管自己,就会说我在家白吃白喝没有钱出去玩,让我赶紧去找工作。”于悦听得最多的就是,“你有本事不要我们管”,“你有本事自己挣钱”。
在豆瓣小组“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”,近4000名网友在小组内分享自己的日常,他们有的像念安一样,认为在全职陪伴父母的过程中疗愈自己,也有人表示“家里没钱怎么当全职孩子?”,还有人对成为全职儿女这件事感到期待和困惑。

他们更多的相同点在于,成为“全职儿女”的过程中,享受着父母提供的安稳生活,也面临着双重的焦虑:既有啃老的情感和经济压力,又有不知何时上岸的心理压力,只能在其中寻找微妙的平衡。
40岁,她裸辞在家当“全职女儿”
成为“全职女儿”之前,念安在一家单位工作了15年。但在2022年岗位调整的时候,她被调去了新的部门:工作繁琐,内容冗杂,专业性强,压力大,24小时待机值班。
尝试做了半年多,念安觉得自己不太能够胜任,“别人都在休假或轮番值班,我却需要每天工作,有一次甚至崩溃大哭。”加上在同一个单位长久工作下衍生的懈怠感,她萌生了辞职的想法。
40岁,从工作了十几年的单位离开,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从作出决定开始,念安每天都处于焦虑的状态中:不断做决定,再否定自己,继而重复这个过程,心力交瘁。
父母心疼不已,主动提出,“要不就离职吧,我们养你。如果有更合适的工作,你再去上班,不想上班,就在家陪我们。”
在北方小镇退休的父母,退休月薪加在一起近万元,听起来虽然不多,但很多年轻人月薪都不能过万,甚至有些双职工家庭月薪也勉强过万。
在家人的一致同意下,念安辞去工作,正式成为一名“全职女儿”:父母每月给她开4000元的工资,要求早上陪跳舞1个小时,上午陪买菜,偶尔陪逛街,负责处理家里所有跟电子相关的东西,以及晚上和父亲一起做晚餐。
除此之外,每个月为家庭安排1-2次旅游,并兼职司机岗位,剩余的时间则由她自己进行支配。
听起来满满当当,但事实上相对于大多数全职儿女充当“被规定工作内容的保姆角色”来说,念安的工作内容更多是陪伴和精神慰藉,她的父母身体健康,有着自己的日常爱好,并不需要她进行照顾,甚至会反过来照顾她,“妈妈会邀请我和她一起跳舞,邀请我共进晚餐,有时出去买很多菜和水果,还要特意跑到我家给我送过来。”
而念安要做的,无非是去妈妈家晚餐时带一点小礼物。她负责打下手,父亲则变着花样做拿手菜,看着母女两人狼吞虎咽,父亲会倒上一盅白酒,半眯着眼睛享受这天伦之乐,妈妈再聊聊过往的事情,兴之所至时,可以聊上二三个小时。
刚从职场退下来的时候,念安还有些不适应,她总想再抓住些什么,于是主动去做副业,“最大程度地心理压力来自想做副业多赚点钱”,但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时候就会非常轻松,她会放下手头的事,刻意去融入全职女儿的职业中。
父母任劳任怨沉浸于爱她的感受,给了念安一种安全感:就算失去工作,也能舒舒服服、没有任何压力做她想做的事。
在念安看来,做全职儿女需要足够的经济底气。工作的15年,她和父母买了房子买了车,还有了一定存款,家庭氛围越来越好,和家中积蓄越来越多也有关系,没有生存的压力,父母又都有稳定的退休金。“如果不是因为有这样的基本保障,我也不敢随意辞职。”
在24岁等待一场上岸
最大的难题是交社保。
2022年6月,于悦失去了两年应届生的资格保留,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,一个月近800元,一年就是接近1万元,对于现在的她来说,这笔支出几乎已经快要承担不起了。
与念安一样具备一定经济能力再从职场上退出成为“全职女儿”的经历不同,更多的年轻人与于悦的情况相似:豆瓣小组“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”的讨论区中,不少人在为灵活就业的社保缴纳发愁——这几乎是“全职儿女”面临的一个普遍性困局。
在于悦的故事里,成为“全职女儿”更像是“被迫”的。2020年6月从一所985院校的管理专业毕业之后,于悦并未得到心仪的offer,彼时正是疫情的第一年,她深觉就业机会渺茫,加上同学不断传来上岸的好消息,于悦思索过后,收拾行囊回到湖南老家备考。
她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“全职女儿”。刚毕业回家备考时,她尚且没有什么经济压力,绝大部分的时间以在家专心备考为主,生活被考公、考研、考各种各样的证书填满。
母亲一开始是全力支持的,什么活也不让她干,只让她专心读书。但眼看着一次又一次失败后,他们没有逼于悦再去考公,而是劝她,“找公司上班,国企私企都可以。”
但于悦铁了心要继续考,她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以应届生身份进入“大厂”的机会,“每次面试都会被问到毕业的这几年在做什么,别说是几年了,现在的求职环境,哪怕你职业经历空窗两个月都有可能成为被刷下去的理由。”在她看来,考公是当下唯一的选择,“只有公务员考试不会在乎你在家备考这段时间有多久。”
在职业规划方面,于悦的目标清晰,态度坚定,但在家庭生活方面,她并没有“全职儿女”定义中那样清晰的以劳动换取报酬。
母亲并不会主动给她钱,她也羞于开口索要。在两年应届生资格保留期间,于悦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各种短期兼职和上门家教,以及生日和节日时,父母亲朋的红包,这些收入的大部分也都用于购买备考资料和支付考试报名的费用,“最难过的时候可能就是看到了一条非常非常喜欢的裙子,但我没有钱去买。”
但“全职儿女”所带来的压力是她没有想到的,从开始需要缴纳社保,母亲的抱怨就与日俱增,开始变得挑剔和苛刻,“她经常说想去旅游但不能去都是因为我,如果我说我可以自己管自己,就会说我在家白吃白喝没有钱出去玩,让我赶紧去找工作。”于悦听得最多的就是,“你有本事不要我们管”,“你有本事自己挣钱”。
她最开始可能还会反驳一下,后面就听着不说话,在“手心向上”的处境里,任何的反驳都是苍白的。
于悦开始在备考间隙马不停蹄的投简历,不停的刷新招聘软件,但在外人看来光鲜的“985”学历并没有在求职过程中为她加持光环,她没有收到合适的面试通知,母亲的斥责几乎成为常态,甚至在外人面前公开讽刺她,“甚至有一次在工人安装热水器时,她说有门手艺也很好,我们家这个读了这么多书还不是没工作。”
所幸在今年春天,于悦收到一个好消息,她选择范围内的一家公司发来了录用通知,虽然并不是她喜欢的岗位,但算是在父母那边有了一份交代,也能够短暂缓解她的经济压力。
话筒里的她语气很慢,但很坚定,“公考的年龄要求是35岁,我想我会一直考下去。”
“全职儿女”与“啃老”没有明显分界线
成为“全职儿子”之前,甄君子在大概接近一年的工作时间里,跳槽了四五家公司,最短的上午入职,下午就离职了。这段经历让他得出一个结论,“作为infp(MBTI16型人格测试中的一种)的我非常不适应职场氛围。”
辞职后,甄君子原本准备继续从事自由职业,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“北漂”,但彼时疫情等复杂原因交织,两个月之后他还是决定离开,先后去了大理、杭州、成都等地旅居,最后一站是大理。
年后,甄君子离开大理回到温州老家,成为“全职儿子”。
父母很满意儿子的决定——作为家里的幺子,甄君子的上头有两个学霸姐姐,往年他们只能在春节和儿子待上几天,日常的亲情连接都靠手机完成。儿子愿意回家简直再好不过了,他们甚至不需要他做什么家务,只要每天陪在他们身边就挺好。
但一点儿家务不做也不太现实。甄君子通常每天会做一到两顿饭,再做一下家里的卫生打扫,当事情都完成之后,他就在房间里泡上一杯茶,打打游戏,再研究一下自己的副业,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家人为其支付工资,甚至他偶尔会支付给父母生活费。
甄君子显然享受这种状态,周末一家团聚的幸福体验让他的精神生活富有了许多,“不用朝九晚五,不用加班,随心所欲睡到自然醒。”偶尔会感觉有些无聊,这时候他一般选择和姐姐出去吃个饭,玩一局剧本杀,“生活就会有趣很多。”
在甄君子的理解中,“全职儿女”也有自己的劳动付出,大部分只是在职场上太过疲倦,回到家中进行短暂的疗愈。当然,在这个过程中,必须是要付出一定劳动、听取父母的要求,而不是一味摆烂。
“网络上说,全职儿女就是好听的啃老。”甄君子对此非常不认同,他认为更应该多思考大环境的问题,而不是将原因全部归咎于个人,“全职儿女也有自己的劳动付出,大部分只是累了,想要静静。后面还是再回到职场的,没必要把人逼那么紧。”
对于未来,他认为自己不会再进入职场,而是在旅居和全职儿女两种形式之间反复穿插。
但在“全职儿女”逐渐普及化的当下,它的出现也更多是在网络平台,对于大部分人来说,“全职儿女”与“啃老”之间并没有过于明显的分界线,“全职儿女”们也无法做到对每一份质疑都慢慢解释,就像甄君子所言,“我会说我是自己创业。”
念安的社交生活中,没有人会问及太多的隐私,她也不会主动谈起,只有很好的朋友日常中会聊到很多,也都支持和赞同拥有自己的活法,但她也明白像她这样的全职女儿还是少数,“大多数的人还是会选择在社会里成长、历练,毕竟人是社会性动物,需要共同成长。”
但她仍旧认为不排除这是个新兴产业,就像全职妈妈、全职保姆差不多,有人提供钱,有人提供服务,有人愿意做,也有人不愿意做,只是一种工作方式而已,和其他的工作没什么区别。
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对此做出见解,他认为“全职儿女”的关键在于每个人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同,自身的发展追求也不同,是一种个体的选择。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,今后可能会有更多年轻人在权衡自己的工作、生活与家庭的需要之后,选择做“全职儿女”。
“这也是当代年轻人工作与生活方式多元化的一种体现,无需用所谓的主流成才观对此抱以偏见,更不能歧视。” (说明: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;本文配图与文章内容无关。)
-
 深圳多家银行超5万元取款需预约 到底是什么情况?2024-06-14 07:53:04深圳多家银行超5万元取款需预约 到底是什么情况?北京银行、兴业银行、光大银行在深圳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均表示,规定取款5万元以上要提前一天预约,是避免客户临时来网点取款,而柜台出现现金不足情况,导致影响储户取款。储户在预约时留下个人信息,即可在指定时间取款。邮储银行深圳某网点负责人表示,若是邮储银行的储户,需在15点前预约次日取钱时间。
深圳多家银行超5万元取款需预约 到底是什么情况?2024-06-14 07:53:04深圳多家银行超5万元取款需预约 到底是什么情况?北京银行、兴业银行、光大银行在深圳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均表示,规定取款5万元以上要提前一天预约,是避免客户临时来网点取款,而柜台出现现金不足情况,导致影响储户取款。储户在预约时留下个人信息,即可在指定时间取款。邮储银行深圳某网点负责人表示,若是邮储银行的储户,需在15点前预约次日取钱时间。 -
 晚霞与闪电惊艳“同框” 实在太罕见了2024-06-14 07:49:53晚霞与闪电惊艳“同框” 实在太罕见了近期,北京雷雨天气较多。13日,粉紫色、橙红色晚霞再现北京,扮靓天空,惊喜的是闪电不经意间与晚霞同框。
晚霞与闪电惊艳“同框” 实在太罕见了2024-06-14 07:49:53晚霞与闪电惊艳“同框” 实在太罕见了近期,北京雷雨天气较多。13日,粉紫色、橙红色晚霞再现北京,扮靓天空,惊喜的是闪电不经意间与晚霞同框。 -
 草鱼身卡异物疑似金镯 实在太罕见了2024-06-14 07:43:54草鱼身卡异物疑似金镯 实在太罕见了6月13日,河南新乡,有网友发视频称一条鱼被疑似手镯的圈子给卡住,画面中圈子将鱼挤压,圆圈处还有血迹,但是鱼依旧活蹦乱跳,评论区纷纷留言“自带赎金必须放生。”好奇鱼的后续处理。
草鱼身卡异物疑似金镯 实在太罕见了2024-06-14 07:43:54草鱼身卡异物疑似金镯 实在太罕见了6月13日,河南新乡,有网友发视频称一条鱼被疑似手镯的圈子给卡住,画面中圈子将鱼挤压,圆圈处还有血迹,但是鱼依旧活蹦乱跳,评论区纷纷留言“自带赎金必须放生。”好奇鱼的后续处理。 -
 虾:我不是红了 我是熟了 这也太可惜了2024-06-14 07:40:23虾:我不是红了 我是熟了 这也太可惜了中央气象台连续多日发布高温预警,多地气温突破40℃,局地还可能破纪录 在高温天气下,虾塘或养殖容器的水温可能会迅速上升,超过虾的适宜生存温度。这可能导致虾出现应激反应,甚至死亡。同时,高温还可能导致水质恶化,增加虾的疾病风险。
虾:我不是红了 我是熟了 这也太可惜了2024-06-14 07:40:23虾:我不是红了 我是熟了 这也太可惜了中央气象台连续多日发布高温预警,多地气温突破40℃,局地还可能破纪录 在高温天气下,虾塘或养殖容器的水温可能会迅速上升,超过虾的适宜生存温度。这可能导致虾出现应激反应,甚至死亡。同时,高温还可能导致水质恶化,增加虾的疾病风险。